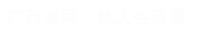审查与感知控制 , 是我们所熟悉的 。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描绘的“电幕”装置 , 兼具两种功能 。 一方面 , 电幕像摄像头一样 , 思想警察坐在中控室里观察着每个人的行为举动 。 “即使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 他也永远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他的友谊 , 他的休闲 , 他对妻子和孩子的行为 , 他独处时脸上的表情 , 他在睡眠中的喃喃低语 , 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 , 都在被不信任地审查着 。 ”今年“3·15”晚会上曝光了“行走的窃听器”——儿童智能手表 , 表明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并非虚幻 。
另一方面 , 电幕控制了信息渠道 , 让人们不断暴露于宣传和叛徒的“自述”下 , 从而变得麻木 。 奥威尔的想象 , 基于20世纪的窃听装置与大众媒体 。 窃听员与报社编辑虽然隐匿在大众视野之外 , 仿佛在暗室中编织着操纵与阴谋的罗网 , 但毕竟是具象的、可理解的个体 。 受众可以将种种情绪聚焦于他们身上 , 并幻想着只要铲除或改造他们 , 社会就会变好 。
21世纪的审查与感知控制 , 采取了更日常化 , 但也更彻底的形式 。 萨斯坎德举出了一款能够迅速识别并屏蔽违规消息和文章的即时通讯软件 。 在算法的加持下 , 数字审核达到了历史上一切审核机制梦寐以求的高度;在算法的帷幕后 , 审核的标准也变得愈发模糊 。 用户对自己生成的数据毫无掌控力 , 而数据却被实时用于规训和审查用户 。
此外 , 正如萨斯坎德所说:“行使这种权力的不一定是国家 。 各行各业的服务商都可以坚持一定的评级 , 这增加了这些服务商的权力 , 而相应地减少了被评估者的权力 。 ”这里点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治理主体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关 , 而是必然会分散到其他主体中 。
我们常常笼统地将这些主体称作“资本” 。 为此 , 西方也有“国有化”的呼声 , 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约束资本 。 萨斯坎德正确地指出 , 根源不在于名义上的所有制 , 而在于算法本身 。
但是 , 算法的威力在“武力”领域体现得最为鲜明 , 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抵
传统上 , 武力与强制都是国家的
只有申诉需要人工处理 , 而且客服人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判决是平台自动得出的” 。 这些“局部性”的代码法律运行良好 , 而且正如萨斯坎德所说:“数字法律 , 私有化的力量 , 自主化的武力系统 , 这些都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过去思考武力运用的方式 。 ”
打败算法克苏鲁在我们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 , 心中不时会飘过一丝
- 华为云&易观分析《互联网出海白皮书2022》
- 网络安全|一年豪掷3000亿搞研发,互联网公司谁更“支棱”?
- 企业微信接口「涨价」,真的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吗?
- Java|互联网/软件/IT行业真的是高薪行业吗?除了卷还是卷
- 飞书|飞书功能添一“人”,互联网招聘管理再上一台阶?
- 高通骁龙|近期最超值的三款新款骁龙870手机 性能稳定高性价比价格真的便宜
- 快手视频|你每天在蚂蚁森林积攒的能量,最后真的被用到了保护环境上吗?
- 魅族|魅族19SPro全线升级,16GB+骁龙8Gen1plus,魅族真的用心了
- 爱奇艺|面试热点:“互联网+护理服务”大有可为
- 互联网医疗|小米12直降800元,4nm+50W无线快充,618活动价仅售28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