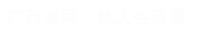如果婴儿期的记忆对我们至关重要,那我们为何会遗忘它?( 二 )
这个关乎神经可塑性的发现令人着迷 , 但也敲响了警钟 。 儿科医生早已发出警告 , 儿童们玩耍的时间及其自由时间变少了 , 他们久坐不动的时间正变得前所未有地长 。
一个多世纪以来 , 像乔恩一样记忆缺失的人们为科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记忆的新途径 。 科学文献中最著名的遗忘症案例或许就是H.M.了 。 他最先是一位癫痫患者 , 后来在1950年代 , 也就是他27岁时 , 他的部分颞叶被通过手术移除 , 他也因此失去了获取及提取情景记忆的能力 。 正是H.M.的案例使得科学家们发现 , 海马体是情景记忆的源头 。
有意思的是 , 我们其实都像H.M.和乔恩一样 。 谈及生命中最初那些年的记忆 , 我们无一不是遗忘症患者 。 我们没法回忆起2岁以前的事情 , 而直到6岁以前的记忆也都十分粗略和不可靠 。 这个奇怪的现象叫作婴儿期遗忘(infantileamnesia) , 这之后是童年期遗忘(childhoodamnesia) 。 几十年来 , 它们在人类及其他物种(从大鼠到灵长类)中的普遍存在一直都是个谜 。
天普大学空间智力与学习中心的首席研究员纽科姆说 , “大家都觉得人生最开始那两年太重要了 。 可是 , 如果我们都没法记住这两年 , 它们又是怎么个重要法呢?对于这个问题 , 我们确实有一些答案 。 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晰干脆的答案 , 那意味着 , 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是太少 。 ”

文章图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命名了婴儿期遗忘 , 并将其解释为一种压抑(repression):大脑会避免婴儿时期的欲望和情绪进入成人的心灵 , 而心理治疗则可以再次通向那些欲望和情绪 。 后来一些针对婴儿期遗忘的解释都试图反驳弗洛伊德的看法 , 并提出另一种假设:语言习得让儿童有了长期记忆的能力 。 但也有其他表现出婴儿期遗忘的物种压根就没有发展出语言 , 因此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仍存疑 。
1978年 , 神经科学家林恩·纳德尔(LynnNadel)和约翰·奥基夫(JohnO’Keefe)出版了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 , 《海马体作为认知地图》(TheHippocampusasaCognitiveMap) 。 它提出一个理论:这个形状像海马一样的大脑结构是大鼠、人类以及其他动物对环境进行表征的地方 。 这些认知地图为空间记忆、定向和导航提供了基础 。 值得注意的是 , 空间记忆系统正是从我们自传式的回忆中提取出了用于存储情景及叙事方式的素材 。 的确 , 我们对经验的记忆总是注入了时间-空间的背景 。 当我们回忆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 我们就会进入一次精神上的时间旅行 , 将过去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在脑海中具象化 。
奥基夫早期的一个发现支持了这个理论:大鼠的海马体中有一类他称之为位置细胞(placecell)的神经元 , 当动物处于陌生或熟悉的环境中 , 这类神经元都会放电 。 不同的位置细胞在一个环境中不同的地方活跃 , 并共同形成了认知地图 。 这项发现让奥基夫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奖* 。 在他之后 , 其他科学家们又发现了海马体中其他用于空间记忆和导航的重要细胞 。 这些细胞包括:根据在水平面上我们的头部朝向何方而放电的头向细胞(head-directioncell) , 以及当我们在一个环境中漫步时放电并建立起坐标系的网格细胞(gridcell)** 。
移动、探索、陌生或熟悉环境中的经验都会让这些细胞放电 。 有证据表明 , 环境的丰富和复杂程度都会影响神经元的数量 , 进而影响海马体的体积 。 比如在1997年 , 就有研究者发现 , 在丰富环境***(纸管、筑巢用的纸条、滚轮以及可以重新排列的塑料管)中探索过的小鼠比对照组多长了4万多个神经元 。 这些新增加的神经元让它们的海马体的体积增大了15% , 并且让它们在空间学习测试中的表现有了显著提高 。 研究者们总结道 , 是神经元、突触和树突数量增加的共同作用让这些动物们在测试中的表现大大提升 。
- 副董事长|京东方A董秘回复:公司与全球数千家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 电池|vivoY55s,能有效解决你的续航焦虑!
- 加盟行业|原来加盟行业是这么玩的!
- 京东|适合过年送长辈的数码好物,好用不贵+大牌保障,最后一个太实用
- 儿童教育|首个播放量破 100 亿的 YouTube 视频诞生,竟然是儿歌
- 苹果|国内首款支持苹果HomeKit的智能门锁发布:iPhone一碰即开门
- 小米科技|预算只有两三千买这三款,颜值性能卓越,没有超高预算的用户看看
- 苹果|苹果最巅峰产品就是8,之后的产品,多少都有出现问题
- 普莉希拉|祖籍徐州的普莉希拉,嫁全球第5富豪扎克伯格,坐拥6530亿被说丑
- 攻克|打破日本垄断!售价7亿元的设备被中企攻克,已开始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