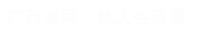k谷歌健康「分拆」内幕:憋屈的CEO、傲慢的Jeff Dean、狂热的AI信徒( 四 )
有消息表示,即便如此优秀,她也并没有经过正规实习医生的训练。在美国,MD/PHD不等同于医生。
而谷歌招进了一批与Lily Peng境遇相似的人:念完医学博士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能成为医生。虽然这些人的思维不那么传统,但是仍然和主流意义上的医生有很大的隔阂。
此外,谷歌做医疗的一大策略,想借各种合作机会和渠道拿到数据源,打造数据壁垒。所以,谷歌需要有一大批的医生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标注。
坊间有戏言:谷歌健康里90%的人都在做数据清理工作。一些年轻医生挣得不多,就会接受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的邀请做数据标注、挣点外快。因此,这些医生团队与工程团队,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
以上种种,就进一步造成了,谷歌健康创新力的不足,尤其和DeepMind对比。
谷歌Research团队在《Nature》、《Science》等杂志及其子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Greg Corrado主页中的很多文章都是如此),没有实质的研究方法创新,而是套用谷歌已有的模型,在内部数据集上做的训练和验证。而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大部分也是因为数据处理地非常干净,但是,干净的数据本就与真实的临床场景不吻合。
“他们的人很聪明,但是有钱、有GPU,有人来标注,一切得到的太容易,就很难从算法层面进行钻研。这也是谷歌健康在《Nature》、《Science》发文较多,但是在CVPR、MICCAI等行业顶会上发文较少的原因。”
因此,谷歌健康的这些重量级临床文章在美国的医学界和科学界,评价不是太高,也有不少的质疑。
LeCun当年就发推吐槽,认为纽约大学规模更大的乳腺癌钼靶AI工作只发表在IEEE Trans Medical Imaging上,而谷歌对应的更小病人规模工作竟然可以发《Science》、《Nature》,并不能服众。
另外,当年Google有一篇被MICCAI拒掉的论文(https://arxiv.org/pdf/1703.02442.pdf),被多家“御用媒体”宣传成病理影像AI上的重大突破。后来,病理AI公司Paige的创始人Thomas Fuchs在GTC的大会上,对Google的这一行径公开吐槽,直言“谷歌解决的只是临床病理里的小儿科”。
重数据,而轻方法,“用暴力计算可以解决”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谷歌健康。
早前,斯坦福的李飞飞曾说:“ImageNet 思维所带来的范式转变是,尽管很多人都在注意模型,但我们要关心数据,数据将重新定义我们对模型的看法。”
李飞飞这样的大牛都是这样的看法,其他硅谷巨头的工程师们,又会有何异议?
互联网巨头的“失落”与“起色”
谷歌宣布健康部门调整的那一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不乏几位业内大咖的评论。
Prisma Health首席数字官尼克·帕特尔博士对谷歌的调整并不感到惊讶,“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行业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有太多复杂的变量需要解决,医疗技术领域已经太拥挤了。”
即便如尼克·帕特尔所说,但是像谷歌一样押注医疗的巨头众多,但是成功者寥寥。
数据隐私问题,让微软的Health Vault在2019年关闭;亚马逊推出的Amazon Care几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员工人数扩展问题;今年2月,IBM兜售IBM Watson。
再比如,曾想招募David做CEO的医疗保险公司Haven,在成立之初都没有确定名称、总部、CEO、长期管理团队以及使命。去年5月到12月,Haven失去了21名员工,公司只剩下59人,很多岗位的负责人都已经离职。
科技巨头,为何做不顺医疗?
首先,这些公司的核心任务是在尽可能向不同领域的客户销售软件和硬件,医疗自然不例外。然而,在大公司里,医疗只会得到CEO的部分关注,也只占整个公司资源的一部分。
- 40K:Battle|VR动作射击游戏「Warhammer 40K:Battle Sister」即将登陆Steam
- Games|Beat Games透露VR音游「Beat Saber」全新音乐方块类型
- 36氪5G创新日报0112|福建省首个“5G+VR”英模会客厅正式上线;齐鲁医院健康管理中心“5G+ 5g
- 「有料评测」100度开水10秒速冷 美的凉白开智能即热水瓶评测
- 飞利浦·斯塔克|「手慢无」泰坦军团 C30SK PRO显示器 秒杀1299元
-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单姗 单文玲 潍坊报道为助力企业健康快速成长|“小巨人”华特磁电“磁”实发展 跑出潍坊制造业加速度
- Pixel|2800元的谷歌Pixel 5a成老外眼中最好的手机之一:可惜没人关注
- 谷歌Pixel|谷歌Pixel 6 Pro经常没信号:官方推送更新修复
- Java|假如让谷歌浏览器进入中国市场,国产浏览器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 「白海科技」完成数千万元融资,定位云原生36氪首发 | 生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