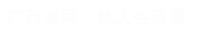dn我们成为技术物种的时代正在来临吗?( 五 )
创造积极技术未来的愿景
如上所述,对于一种也许很快就有能力破坏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的技术,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而科学家、艺术家与民众关于这种能力应当如何被控制以创造更好世界——一个生命有更多可能、更公平也更有意义的世界——的零星尝试,与这种恐惧共存。
在这个复杂的场景中,我们失去方向的希望、恐惧与努力, 正在奋力孕育出让我们得以生存的新文化。对于我们有可能定居的未来,我们该如何构建叙事与愿景?我们该如何设想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够朝着它的实现努力?
西方社会对技术的恐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正如玛丽·雪莱在其著作《弗兰肯斯坦》(1918 年出版,雪莱时年20 岁)中精彩总结的那样,出现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蕴含的苦涩在很多西方人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与技术有关的伤疤,后来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预测未来的学术新作品,以及无数反乌托邦未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中,这些源于盎格鲁中心经验主义的叙事仍然很流行。
其他西方国家对技术具有非常不同的经验。在我的祖国西班牙,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对技术充满厚爱;无论主人的社会出身如何,屋顶上的一片太阳能板都会被骄傲地展示,作为解放现代化的一种标志。然而,让我震惊的是,我经常在英国的农村地区听到,人们认为屋顶上的太阳能板看起来是“可怕的现代化”,觉得它破坏“乡村生活”的体验。这不只是出于审美的原因,更是出于对技术的厌恶。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对文化和学术写作拥有主导权,它传播了一种很特别的看待技术的态度——这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演化而来。如今,这种负面的观点又与“不稳定”的文化基因以及大部分存量就业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心态形成共鸣。这种负面预测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对未来没有准备,如果对于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愿景,用任何办法都不能塑造未来。
在那些将科学视为福祉来源的国度里,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日本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巧妙地驾驭了复杂的地缘政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要归功于基于技术发展的增长策略,还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失业率,以及在工人(大多数是男性)及其家庭中对财富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技术被认为是一种通向更好未来的推动力, 这种思潮不是只出现在日本,而是在东亚地区普遍扩散。许多现代的流行文化都相信未来人类、自然与技术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日本的小说中也很少会出现弗兰肯斯坦式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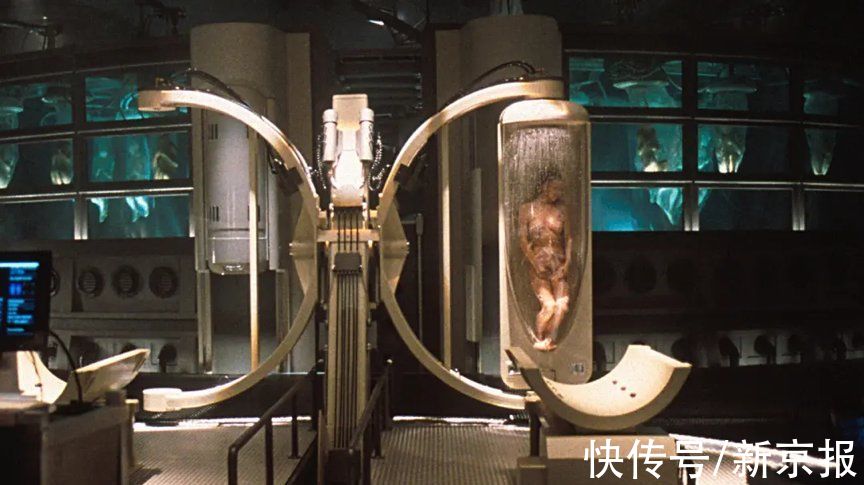
文章插图
电影《第六日》(2000)剧照。
尽管当前的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创新的停滞,这源于对移民、性别不平等与极低出生率的恐惧,但其国民对于积极转型的期望仍然与技术交织在一起。我想和读者们分享一个来自日本的案例,它是一种进步的、富于创造性的推动力,发现了利用技术产生积极文化的方法。这个榜样也许能够启发我们,让我们思考自己对未来的愿景与梦想,那是一个我们为自己索求的未来。
2001 年,当猪子寿之从东京大学数学工程与信息物理系毕业时,他创建了teamLab公司。“科技改变世界,艺术改变人类思想……与价值”,这句箴言让他着迷,于是他致力于创造数字艺术,“为当代社会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他的梦想是和朋友们一起生活并创作,于是他创建了teamLab。如今,teamLab已经成为拥有数百名“超技术专家”的社团,包括程序员、工程师、数学家、建筑师、计算机图形动画师以及其他专家,他们在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一起工作,共同从事商业和艺术运作。
- text|《2021大数据产业年度创新技术突破》榜重磅发布丨金猿奖
- 传感器|称年轻,我们怎么做到经济自由?
-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瞧不起中国芯?芯片女神出手,30岁斩获国际大奖,让美国哑口无言
- 元宇宙持续发酵,或迎“终极形态”?马斯克为何力挺脑机接口技术
- 我们的生活|社交正在推动“孤独生意”多元化发展,天聊将重塑用户精神世界!
- 自动驾驶|华为首秀自动驾驶,王兴:特斯拉遇到技术与忽悠能力相当的对手了
-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地震救人新突破!中科院研制出触嗅一体智能仿生机械手
- 军工|中国版“英伟达”诞生,核心技术完全自研,国产替代即将崛起
- 电子封装技术、微电子、集成电路等,电子信息类专业,研究方向
- 单片机|OPPO最新实验室曝光: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打造,将加速新技术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