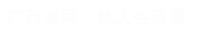刘美香不大喜欢人类,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具体表现为它没有太多耐心接受我的抚摸,而朋友来我家看猫,则有几个固定的观赏点:沙发底下、床单底下,或者衣柜与墙的空隙里。
我以刘美香的母亲,更准确地说,以它的养母自居。刘美香的生母叫大黄,是我前司所在园区里的物业老板养的猫。物业老板看起来是个动物爱好者,仅我在园区的一年里,就看过他养猫、浣熊、羊驼以及两只柯基。
大黄没做绝育,在2019年春天生下一窝染病的小猫。它和它的孩子因此被抛弃。我只知道有只小猫被同事领养,来到秋天,还剩一只眼睛生了病的小猫跟着大黄,而大黄又一次怀孕。
刘美香就在第二窝小猫中。我遇见它时,它大概有两个多月大,瘦瘦小小的,但因为从小在街头混着,既警惕又凶悍。我用猫粮引诱着它靠近,然后一把拎起它的后脖颈,塞进猫包,打车回家,把它关进提前准备好的笼子里。
它在笼子里嚎叫,连续两天不停。我把它放出来,收起笼子,它迅速窜到窗帘上头。又过了几天,它转移阵地,藏到柜子后面。养猫前两周,我只能通过碗里每天减少的粮和水来确定我真的养了猫,并且,猫还活着,在我的家里。
“要控制自己的控制欲,凭什么圈养人家还要求感激呢?”2019年12月初,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朋友劝我,别对猫有太多期待,它只是你的合租室友。
就在第二天,猫爬上了床角,藏在被子后头。我看见它毛茸茸的耳朵,像露出海面的鲨鱼背鳍。平静之下暗藏凶险,我想摸它,它毫不犹豫地挥拳。这拳基本夯实了它的“猫设”:拳王美香。几个月后,拳王美香迎来高光时刻:以6斤的小身板对两只10多斤的公布偶猫重拳出击。
要等熬过2020年初那个漫长的春节假期,在分别20多天后,我和猫反而开始熟悉起来。回京当晚,猫绕着我打转,蹭我的腿,靠着我的手臂打呼噜,同时不忘初心,时不时也要打我一下。如果套用人的行为逻辑,这种状态或许可以理解为:爱恨交织。
一位“宠物侦探”告诉我,搬家是导致宠物丢失,以及“被丢失”的最重要因素——人类想要更好的生活环境,但猫狗并不理解,它们被迫来到新家,克服恐惧,适应环境,直到下一次搬家。
找到这位宠物侦探,正是因为我在搬入上个新家的第一天“弄丢”了我的猫。或许是我无意间开过窗户,猫咪趁机逃走。比这更可怕的猜想是我下楼扔过两次垃圾,也许猫咪钻进了纸箱里,又被我亲手抱到楼下送给了收废品的阿姨。
郑执有一篇叫《霹雳》的小说,主人公是个没有工作且写不出东西的文字工作者,他搬进新家没多久,猫没了,生活开始加速失控。
故事里猫咪在主人公的一次打骂后出走,我记得几天前我也骂过我的猫。具体原因忘了,但大多数情况下,猫会在我强行抱她抚摸她时变得凶悍。幸福它配不上我,故事结尾说。我忍不住看窗外的空调外机——那是主人公最终发现猫咪尸体的地方。
下午六点左右,我在淘宝上联系到了那位侦探先生,选了最便宜的套餐,4500元。根据流程,我要等他上门来签合同,付2000元定金。
这笔开销意味着我要放弃为新房间添置物件的打算,并且尽快找个班上。七点出头,侦探打来电话。赶上限行,他的车被拦在五环外。据说找猫的黄金时间是猫走丢后的72小时内,我既想他来得快点,又隐约希望他来得再慢些。
前任租客突然发来信息,告诉我卧室的地台是空心的。我把手机塞进地台边缘的缝隙,打开前置摄像头。屏幕里出现了一根筷子、一把钥匙,半截铅笔,以及一段团缠绕着灰尘木屑的头发。台面上铺着虎纹地毯,内里则是各种垃圾,就像是我北漂生活的一体两面。我转动手机,不断调整角度,地台深处有两块蓝绿色的光斑。那是猫眼睛的反光。
- 电池|电池为信息保存提供电源,如果没有电池,计算机中就没有时间概念
- 科创板日报|游戏工委相关人员回应“2022年不新发游戏版号”:没有这样的消息
- 微信|微信“精简版”来了,没有朋友圈,更没有广告
- 小米科技|没有患得患失,从不畏惧失败,没有钱的马云也很强大
- 土巴兔|没有一个年轻人能躲过装修的坑
- 华硕|几乎没有短板!华硕TUF GAMING B660M-PLUS WIFI D4重炮手主板评测
- 导数|很难想象没有导数的数学和物理学,导数概念背后的直觉及其应用
- 四年从没涨过 斯宾塞表示XGP目前没有涨价计划
- 手机好坏没有固定标准,但是没人认知到,我从大屏手机谈谈本源
- 佳能|佳能后期空间小,主要并不是宽容度问题,而且因为没有iso 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