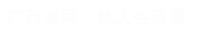文章插图
与此同时,插画师邻居的父亲因心力衰竭受损,母亲因老年痴呆症受损 。他们被困在时空里,尊严被疾病吞噬 。
在冲击下,关于意义的命题第一次跳出了我们邻居的生活经验:如果生命太弱,无法控制,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父亲去世后,邻居拿起画笔,记录了三姐妹一起照顾母亲的艰难时刻,以及父母的爱情故事和一家人的过往 。当被疾病侵蚀得面目全非的母亲面对这些画面时,她突然说我还记得全家人的疗伤之路开始了 。
文王双兴
编辑鱼鹰
由图受访者提供
双重丧失
去父亲的灵堂前,邻居发现母亲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变了 。那是2018年的春天,父亲走了,母亲病了 。几乎与此同时,几十年来一直以恒定速度运行的列车突然脱轨,失去控制 。
去看爸爸吗?女儿们问 。妈妈点点头,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对50多年的夫妻!”盛装准备出门,刚到门口,她突然说了句像是在生某人的气:我不去!
一家人站着不动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叹了口气:“夫妻50多年!邻里又走上前去,试探性地问她是否还想去 。母亲抬起头,像是在征求意见,问道:“那我还是去看你父亲吧 。”没有表情,没有情绪,然后一路平静的走向大厅的入口 。
母亲突然开始颤抖,捂着脸哭了起来:老唐,我来看你了.三个女儿吓坏了,赶紧去帮忙,但更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母亲指着父亲的画像,似乎瞬间恢复了正常 。在父母简短的语气中,她喃喃自语:你爸爸郭(本)张翔,一脸哭相,没有照片 。
情绪翻来覆去,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母亲 。先是惊愕,然后是一寸一寸的悲伤 。——有父亲离去的悲痛,也有母亲失去悲伤能力的悲痛 。三个女儿在灵堂里哭,眼泪掉了下来,是双重的损失 。
n>
处理完父亲后事不久,三个女儿带母亲去了医院,医生递过来的诊断书上写着中重度老年认知症,属于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型 。父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母亲的记忆被一点一点抹除,两个漩涡遇到一起,变成更大的漩涡,整个家被裹挟其中,乱了阵脚 。
1960年代,父母在部队相爱、结婚、生子 。父亲是家里的绝对权威,一家人行动都要听他指挥,只有母亲除外,她一撅嘴,他就没辙了 。两个人感情好得出名,一起看电影,一起做家务,一起跑步,一起骑自行车,直到头发白了,还保留着彼此之间的情趣 。有段时间,父亲看起了台湾言情剧,遇上接吻的镜头,还去逗母亲:他们又抱到一起啃萝卜了,来,我们也啃一下 。母亲就笑,翻一个嗔怪的白眼 。父亲得了冠心病后,两个人开始手握着手睡觉,这样,如果父亲不舒服,母亲就能立刻察觉 。亦邻回忆,舅舅去世时,父母还抱在一起哭,约定以后两个人一起走 。
没人料到会突然被拽进疾病的漩涡 。父亲患上心衰,卧床直到离世;而母亲的情绪,在激动和漠然之间来回切换,有时候踉踉跄跄跑过去,关心、哽咽,但多数时候,是麻木的,不耐烦的 。女儿建议她陪陪父亲,她就听话地坐过去,完成任务一般地随便问一句,然后起身离开 。
最后那段日子,亦邻发现,父亲的病痛越来越严重,而母亲变得越来越淡漠、不耐烦 。有一次,父亲在病床上喊:我想你陪着我,我舍不得你啊!现在我是要求着你了……而母亲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听罢,只站在那里傻笑 。女儿们没有办法,干掉眼泪 。
那年5月,在病床上处于昏睡状态的父亲突然清楚地喊出四个字:准备出发!过了一会儿,又喊了一句:出发!然后离开了人世,终年84岁 。
母亲的病情继续不可逆地发展,很多记忆被抹除,越来越像一个孩子 。
亦邻是位插画师,她把这一切画了下来,连同全家人共同经历的往事 。这是对父亲的纪念,对母亲记忆的唤醒,也是一次与自己成长伤痛的和解 。
王春霞在工作群里看到了它们,当时还没有完整书稿,零零散散的文字和漫画堆在一起 。她拿眼一扫就知道,这不是个省时省力的选题,但还是上头了,成为了这本书的编辑;9个月后,《我还记得》出版 。
阿尔茨海默这个题材的书在国内其实不缺了,但是用漫画的形式这应该是第一个 。王春霞说,她在里面看到了足够丰富的内容,一圈一圈地嵌套在一起,最里层是三个女儿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再往外延是长期的家庭照护,第三层是代际关系,最外层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衰老和死亡命题 。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亦邻漫画,照顾母亲 左滑查看更多&&&
我还记得
父亲下葬前一晚,三姐妹分别和他告别 。到亦邻了,她发现自己很难和父亲对话,脑袋一片空白,最后决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画画 。
生前,父亲始终说亦邻画得不好看,他不喜欢漫画,喜欢写实,而那恰恰是亦邻排斥的 。时隔几十年,童年的隐伤又重新浮出来,亦邻依然想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想要得到认可,她决定画一幅素描,把他最后的样子留下来 。
线条落在纸上,不满意,擦掉;新的线条延展开去,不满意,擦掉 。
画不出来 。亦邻崩溃了 。攥着笔,用力画,又用力涂抹 。突然失控,趴到一旁的先生身上,嚎啕大哭 。
后来的日子里,亦邻开始画父亲 。
做了20几年插画师,但画自己的父母,此前并未列上过日程 。父亲去世后,悲痛之外,总觉得有些含混不清的情绪堆积在那儿,埋怨、自责,或者遗憾?童年时代系在心里的一个一个疙瘩似乎没有机会解开了,宣泄似的,她拿起了笔 。
绘画成了一个出口,亦邻一口气画了好多 。画爸爸教女儿们唱《我是一个兵》,画他补鞋、补锅、打篮球,画他让犯错误的女儿们罚跪、写检讨书……
有一次,亦邻画到父母年轻时第一次登台表演,父亲和几个叔叔一起说三句半,母亲和几个阿姨一起敲碟儿,觉得有趣,随手拿给母亲看 。
生病后,母亲的容貌发生了变化,她不爱笑了,眼角总是垂着,显得凶巴巴的,又像在生气 。但看到那两张画时,母亲突然咧着嘴笑了起来,皱纹堆在一起,拉着亦邻说:郭(这)个,我还记得!
亦邻感到惊喜,也突然意识到,说不定绘画可以唤醒母亲的记忆,延缓她大脑萎缩的进程 。于是,她从画父亲,转而画一家人共同经历的事,画父母小时候的民谣,他们的爱情故事,三姐妹的童年……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致和耐心的妈妈,唯独对这些回应比较热烈,她指着那些小纸片说:我给你鼓掌 。
亦邻开始叫着母亲一起画,一点一点梳理往事的脉络 。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记忆就像一个古老的书柜,最上面的书慢慢被拿走了,但压在底下的被保留了下来 。
一天晚饭后,一家人坐着闲聊,亦邻让母亲讲讲三姐妹小时候的样子,老人想了想,说:老大老实,老二好恶,老三好乖 。然后和三个女儿一起笑 。亦邻建议母亲把她们小时候的样子画下来 。老人从未学过画画,但拿起笔来特别自信和笃定,笔尖按在纸上,毫不犹豫就推出去 。没几分钟,三幅小画就完成了:老大穿着有竖条纹的裙子,老三抱着布娃娃,唯独老二特别,手上抓着一团看不出是什么的线条 。
亦邻问,这是画了什么,母亲张开手指又合上:捏鸭子,鸭子捏得嘎嘎嘎,你都不松手 。亦邻想起,这是有一次经过菜市场,自己抓起了一只鸭子 。再问,有没有其他好的事情可以画,母亲说:没有 。
后来,这些场景也被亦邻画进漫画,新书出版后,被很多读者视为严肃和沉重题材里的幽默瞬间 。但对亦邻来说,把画掀起来,底下是陈年的伤口:不被喜欢这件事让她疼了很多年 。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亦邻漫画里的家庭往事 左滑查看更多&&&
捡来的小孩
亦邻的童年记忆大部分关于乡村 。当时,因为保姆离开,父母决定把女儿送到外婆家一个 。姐姐清雅不同意,还没分别就大哭;但亦邻适应那里的生活,蹦蹦跳跳玩得开心,于是她成了被送走的那个 。
月亮、蜻蜓、独轮车,还有一眼看不到头的田间小路 。乡村生活的快乐是真实的,但情感缺失也是真实的 。父母变得越来越陌生,有时候,亦邻在外面玩,看到爸爸妈妈来了,撒腿就往回跑,钻到牛栏里躲起来 。那些举动里藏着小女孩的巨大心事:亦邻想和父母走,又怕他们不是来接自己的,更怕被接走几天又要再被送回来 。为了不被拒绝,干脆装作不期待 。
五六岁时,亦邻被接回父母身边 。在外婆家时,她还是那个开心就笑生气就闹、脾气上来满地打滚的小兽,但回家后,因为担心再被送走,她突然变得小心翼翼,不笑不闹更不打滚,每天竖着耳朵听爸妈聊天 。小朋友们去捡木蒂坨(树的顶部,锯下来当柴用的)烧火,母亲随口一句我们家孩子还是不够厉害,亦邻第二天就跑去讨好木工叔叔,好带回更多木蒂坨 。
父亲是个军人,喜欢按照部队的方式教育孩子,他很少表示认可,所有指令要求亦邻绝对执行:我在他面前做啥都不对,哪怕洗个菜,他都认为我是错的,要按照他的方式 。
妹妹小菀出生后,亦邻的失落感变得更强 。她足够可爱,会撒娇,赢得了爸爸更多偏爱 。妹妹学跳舞是被支持的,但亦邻学画画却被反对;妹妹出门回来父亲翘班也要去接,亦邻曾凌晨三点一个人拖着行李回家 。很多年之后姐妹聊起父亲,会同时惊讶:我们说的爸爸是同一个人吗?
老二基本上就属于夹心,上面大姐身体不太好,爸爸妈妈都要照顾着她;我就属于小,那也得让着小的吧 。所以她就莫名其妙要变成很强大 。小菀回忆 。亦邻的不满逐渐变成了对姐姐妹妹的嫉妒,然后以欺负的形式发泄出来 。她曾经出主意干坏事,让大姐顶包写检讨、罚跪;也曾经出手打妹妹,小菀至今还会开玩笑控诉,自己挨过的第一个巴掌就是二姐打的 。但也因此,不被喜欢的老二更加不被喜欢 。
那时候,亦邻总听周围人说:你是捡来的,爸爸妈妈都不喜欢你 。叔叔们抱着胳膊,翘着二郎腿,把调侃和挑衅一个女孩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 。
亦邻气不过,歪着脑袋怼回去:爸爸妈妈不喜欢我,我还有外公外婆 。看热闹的人不尽兴,继续说:你外公外婆也不喜欢你,不然怎么会把你送走 。
亦邻站在人群中间,用力想办法抵挡这些中伤,最后装出恶狠狠的样子:都不喜欢我算了,我自己喜欢我自己!
没想到,爸爸在一旁听到这句话很高兴,说亦邻有志气——这是她成长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认可 。装出来的盔甲被当成真的坚强,只能把眼泪憋了回去 。以至于,在后来的岁月里,亦邻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精力,想要确认和证明自己是被爱着的 。
11岁那年,亦邻得了肾炎,医生强调要卧床,不能走路,父亲每天背着她去医务室打针 。路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亦邻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眼睛朝四面八方扫射,总希望能碰上自己的老师同学,希望被看见:我被爸爸背着、宠着呢!
后来,三姐妹陆续长大、离家,童年的伤没机会治愈,被搁置在了那里 。姐姐清雅在外工作几年后回了故乡,亦邻去了广东,妹妹小菀去了北京,天各一方 。几十年里,亦邻和父母最长时间的相处是一个多月——她把父母接到广东的家里住过一次,其他时间,每年春节才回家 。再后来,一家人重新聚到一起,是在父亲的灵堂 。

文章插图
三姐妹和母亲合影
和解
和母亲一起画画的过程中,亦邻聊起了小时候的自己,那个在长辈眼里淘气、像男孩子,但又藏起了敏感和脆弱的女孩 。
母亲说,怀亦邻的时候,人们根据母亲的肚子大小、形状、走路姿势等等迹象,都推测会是男孩 。听到这些,亦邻几十年的困惑才略微有了解答——当一个女孩呱呱坠地,父母心中的期待多少有些落空,于是有意无意在她身上强化对男孩的想象 。整个童年,姐姐和妹妹有洋娃娃,亦邻永远只有木头枪;有一次她被虫子吓哭,为此被父亲打了一顿 。
妹妹出生后,父亲几乎把所有宠爱和温柔都给了小菀,但对亦邻,他希望她坚强、坚硬,能扛起事,也觉得她足够强大,不需要给予太多关注 。在母亲印象里,亦邻一直都不恋家的,至于捡来的、不被喜欢之类的说法,在母亲看来,是逗小孩子玩,没什么大不了 。
在那一天的画后面,亦邻写:上一代人习惯了精神粗粝的生活,他们不理解我为何而痛苦 。
童年的境遇,让亦邻和妹妹有了完全不同的性格 。我在一个雷雨的晚上见到小菀,46岁的她扎着丸子头,穿着吊带和练功服,会因为雷电突然挑起眉毛喔一声,也会在谈及父亲时突然忍不住哭鼻子,我最幸福的是爸爸妈妈对我『自我』的保护,从来没有打碎过 。小菀是现代舞者,她教舞蹈的机构里,有一部分学生是特殊儿童 。排练舞蹈时,她能敏锐地发现某位小朋友情绪的异常,她提起最多的两个词是尊重和接纳 。大概,因为被爱,所以爱人显得轻易 。
但妹妹被温情包裹着的日子,姐姐在用前半生疗愈童年的伤口 。亦邻陪小菀上过课,课程结束后,她抛来一个问句和一个陈述句:为什么你对他们的接纳度那么高?我做不到 。
直到现在,姐妹之间沟通起来,小菀都倾向于拿出来说,但亦邻会突然堵住,然后提出下楼走一走 。小时候爸爸妈妈不接纳她的那一部分,变成了她性格中的一部分,所以只能自己独立地去消化 。小菀说,不论你想或者不想,那些东西真的都存在于你的身体里,在你的一生中去循环反复 。二姐变成记录者之后,算是和爸爸、和童年做一些和解和疗愈 。我觉得谈不上原不原谅,她只是回到那一刻,了解了一些东西,然后把它们放下来 。
如今的亦邻极瘦,甩在旗袍两侧的手臂,几乎和甩在脖颈两侧的麻花辫差不多细,曾经敏感的小女孩到了天命之年,她声音柔和,腰杆挺得直直 。那些和母亲一起拿起画笔的日子里,她看到一条线,把窘迫的、痛苦的、荣耀的,点点滴滴串在一起,让自己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那些曾经介怀的,画下来,好像终于可以松口气,没什么大不了 。
今年4月,三姐妹回故乡,一起给父亲扫墓 。当时,《我还记得》尚未出版,亦邻带了一本样书回去,想要告诉父亲,但站在墓前,依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小菀很难想象,对自己而言非常轻易的事对亦邻来说有多艰难 。当姐姐清雅和妹妹小菀分别和父亲述说完想念以及近况,亦邻都迟迟说不出话,后来直接跪在那里,大哭——从小到大,亦邻都是家人眼中最坚硬的那个,看电视剧时,小菀已经天崩地裂了,亦邻也绝对不会落泪,但在父亲去世后,两代人之间的缝隙,慢慢被眼泪灌满了 。
离开前,姐姐写了一本关于咱们家的书的消息,小菀替亦邻说给了父亲 。

文章插图
《我还记得》
被困住的父母
在亦邻的漫画里,父亲永远高大魁梧,腰杆笔直 。他是抗美援朝老兵,一辈子坚强、刚硬,很少生病,走起路来也风风火火,他最讨厌一个人霉起霉起(没精打采)的样子,冬天,凉飕飕的风往脖颈子里灌,但一旦看见女儿们瑟缩着走路,父亲会立刻皱起眉来,背着手在后面喊:抬头挺胸!
但到生命的暮年,他的腰再也没直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身体疼痛、睡卧不安,父亲只得整宿坐在轮椅上,不停看时间 。回到病床,因为腰痛,总是想不停地躺下、坐起,调整姿势 。最后一段时间,他连坐这项最基本的技能都无法独立完成了,需要女儿把他推起,并在背后用肩膀抵着,才能勉强坐上一会儿 。
生病住院时,父亲抵触一切象征着身体机能丧失的东西,拒绝请护工,拒绝用轮椅,拒绝女儿帮他擦洗身体,更拒绝帮他接尿 。
当时,父亲全身浮肿,呼吸困难,光是站起来都颤颤巍巍,但还是坚持自己弯下腰拿尿壶、自己接尿 。因为双手哆嗦,尿液会不小心洒在衣服和床单上,但他总是坚持躺上去,然后用被子遮掩住,整个房间弥漫着尿骚味 。女儿们想帮他清洗,父亲就大吼:我不要你在这里!
没多久,护士发现了异常,把三个女儿批评了一顿:要是得褥疮就麻烦了!然后一把掀开了父亲的被子,说:都是自己女儿,你怕什么?亦邻看见,父亲皱着眉,闭上了眼睛,把头偏向一侧 。
在亦邻印象里,他讲起过自己上战场的事情,女儿们问,你怕吗,他挺着腰板说,不怕 。当时,他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但几十年后,当自己要面临正常的衰老和死亡,他是无措的 。

文章插图
漫画里的父亲
冲击之下,关于意义的命题第一次跳出在亦邻近五十年的生命体验中:如果生命衰弱到无法控制,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同一时间,父亲被心衰损害了躯壳,困在空间里;母亲被阿尔茨海默病损害了记忆,困在时间里 。但不管是否意识清醒,尊严都被疾病消耗殆尽 。
除了情感的淡漠,母亲的行为也出现了异常 。她年轻时爱美,会绣花,会编织,还会做衣服,也给家里做漂亮的桌布、窗帘 。她讲究得甚至有些保守,经常叮嘱女儿们笑不露齿,走不动裙 。但当疾病慢慢把她的情感和记忆抹除,那些修养、自尊和羞耻心也一同消失了 。
女儿们发现,天一热,母亲就穿着短裤,打赤膊坐在沙发上;她开始喜欢上用手指抠鼻子,然后随手把鼻屎抹在栏杆、桌布或是椅子上;上厕所的时候,还没走到卫生间,就已经把裤子脱下来了,即使不远处就坐着客人 。
母亲似乎时刻处于不安中,时刻需要女儿安排,做任何事都很难持续五分钟以上 。家中的对话时常是——
- 为什么一般不养鹅 特种养殖创业网致富网养鹅
- 创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有哪些,以下不属于融资的创业性来源的是
- 伊隆·马斯克|人工智能后国人在多少年之后将不会写字,马斯克的梦想是否能成为现实?
- 华为云|青少年沉迷短视频,视频号不应继续藏身微信
- 星巴克被指“玩不起”,抖音0.01兑换券被退款
- 小米科技|就叫“十三香”!小米骁龙8Gen2新旗舰不改名,继续对标苹果
- 苹果|为啥很多苹果用户,压根都不会考虑其他品牌手机?
- 刘强东|有情有义的企业家,不止刘强东!
- 唯品会|谁在用唯品会?Q3财报数据出炉,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 |128G的手机是真不够用了!大内存普及还得看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