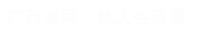两种悲剧(人生只有两种悲剧)这世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求而不得;一种是得偿所愿 。
此言来自奥斯卡.王尔德的喜剧《温夫人的扇子》中、女主人公德温米尔的台词: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
求而不得,和得偿所愿,是我看过的、对其最恰到好处的翻译 。它们是天平的两端,当一端逐渐倾斜,另一端就需要增加重量维持平衡 。
生就的凡胎肉体,是一旦在自己小小的生活里安定下来,日复一日只能接触视线以内的东西,便很难再去看到其他轨道上的事物,无可避免地陷入某种狭隘 。
所以,我们求仁,我们得仁,心里还是会有一只困兽在骚动着 。
不时想从昏聩囹圄的生活中逃离,去追寻另一种更生机勃勃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对于“得不到”的那部分,人们依然充满憧憬和好奇 。
离开此处、去往彼方,是每当天平倾斜时,我们最乐意做的事 。冗长规律的日常给与安全感,而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建筑和历史、相遇和路过,是维持生活鲜活的氧气 。
诚如诗人北岛写道:”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去过哪些地方、做过哪些事,多年后不一定还会事无巨细地记着 。最后残留下抽象的感觉、颜色和一些片段,那些没被大脑抖落的体验,才是离开的意义 。
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体验 。

文章插图
▲▼至少有一半热爱旅行的人都拥有一本白封皮的《在路上》,凯鲁亚克,是一代人对自由这个宗教的信仰 。
一伙青年学生开车横穿全美,最终抵达墨西哥,一路狂喝滥饮,耽迷酒色,流浪吸毒,性放纵,在经过精疲力竭的漫长放荡后,感悟到生命的意义 。
我的那本《在路上》不在书架上,在行李箱里 。大二暑假陪我搭上去往云南昆明的火车 。来回接近90个小时,算上昆明到大理、大理到丽江的中转时长,初次绿皮火车之旅,我一下就把记录猛拉到100小时以上 。
这也是个人第一次独自旅行,10余天后带着一身的紫外线创伤回到厦门,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坐绿皮,和单趟超过8小时的动车 。

文章插图
丽江早晨遇见的狗
现在想起云南,记忆不断重播的片段如下:
1. 青旅里跟我说她差点被货车司机侵犯的西藏穷游姑娘;
2. 丽江古城搭伙吃饭的高三毕业生,在酒吧跟长沙某大学英语老师的艳遇故事;在客栈做义工的计算机系大四学生,晚上做毕业设计,早上6点背着竹编的篓子去集市买菜;
3. 不管晚上下多大的雨,清晨时刻都会出太阳的湿漉漉的大理;
4. 香格里拉旅馆里的老鼠在半夜偷偷把我的充电线给咬成两截,隔天只好满大街找卖充电器的地方 。香格里拉的商场也会放苏打绿的《小情歌》,同时也卖着在沿海城市滞销下架的鞋子 。当地的年轻人开着三轮车在宽敞的路上大声唱歌 。还有,青稞酒酥油茶其实很不合胃口 。
5. 有个姑娘跟我说,每个人都有属性,她的属性是流浪 。
因为一趟占了一年33分之一的旅行,我获得了比余下33分之32更有意思的体验,见识到不同的山海、人文,最重要的是看到了不同种的人生,感叹原来有人愿意选择这样那样的生活,和自己截然不同 。
当然,也会发现心心念念的东西可能落到“不过如此”的境地 。
比如绿皮火车这种看上去充满文艺乌托邦的出行方式,也仅适合存在乌托邦式的想象里:来回每趟40多个小时,充斥着糟糕的臭袜子气味、嘈杂狭隘的环境 。
这时候我唯一感谢的,是凯鲁亚克把《在路上》写得足够长,否则真不知道如何渡过在暮色里缓慢行驶的夜晚 。
但从那以后,我就生了病,一个叫“一段时间不出门就要死翘翘” 的病 。
▲▼▲我很喜欢奥美2016年为全球酒店预订品牌Agoda做的一支广告文案,以《陆潜者》为主题:
旅行的人有两种,他们只会追随热点,浅尝风光,而我们是陆地上的潜水者,我们潜入陆地,从难寻的缝隙,到被旁人忽略的角落,潜入到土地的灵魂所在,因为潜下去,才是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潜得更深,发现更多 。
袁越在《土摩托日记》写:旅行到底有什么价值,取决于你到底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他认为旅行所带来的体验会凝聚成一种能力,“ 当我知道的人类故事越多,我对世界的偏见就越小 。”
就个人有限的体会而言,没有经历过复杂的简单、匮乏而片面 。毕竟,一生不是一场无止尽的马拉松,而是一个圆,在往复循环的进退中,看见其中迂回的道路 。
【人生只有两种悲剧 两种悲剧】曾经看山是山,后来看山不是山,如果你足够聪明,就能辨别出有些是生活不得不撒的谎,然后看山仍然是山 。
- 知足常乐的人生感悟,知足常乐正能量语句
- 语重心长的人生语录 语重心长是什么意思
- 我的硬核人生 天外重生者
- 电吉他价格电吉他推荐 「依班娜电吉他」
- 全力以赴的励志句子有哪些
- 启迪心灵的人生感悟句子 影响一生的心灵感悟
- 人生哲理句子精辟简短,简短精辟正能量的句子
- 拼多多|“中国互联网教父”张朝阳的人生经历
- 人生分为哪些方面 生人包括
- 网站盈利模式其实只有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