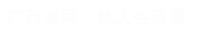其三,人之受尊重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人之所以受到尊重的理由,似乎不再依循友爱与团结的逻辑,而以技术标准设定人被尊重的程序与程度。在传统的神人关系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团结具有神圣的基础。在经典的现代伦理话语中,人之尊重的理由是因为如康德所断言的“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既然所有人都是目的,一个人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特定目的的工具,而必须平等尊重他人,以此而友善相待和团结相处。“人类是道德法则的肉身化,而道德法则的尊严让人类值得被尊敬。他们应该被他人尊敬,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义务尊敬自己。”这是成熟现代即脱离了神的庇佑而呈现的人的尊严状态。但在技术一日千里的飞跃中,技术似乎为人际关系设定了新的规则,接受技术给定程序控制便受“尊重”,便成为社会一员;相反,如果拒绝技术程序设定的规制,不仅不受尊重,而且会因为智能程序被淘汰出社会。这样的结果,当然反映了政治权力与技术权力两方面的意愿,尤其是反映了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意愿。但这种人工智能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友爱与团结所造成的撕裂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现代经典形态的“人的政治”趋于终结。这种终结有其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直接原因是为了“人”的解放,即帮助人类从繁重的日常负担中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以赢得更大的自由,而在物化劳动与社会控制诸方面借助技术手段,因此让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对技术的倚重容易导致对技术的单纯依赖,而技术则反噬人类。随着技术供给解放人的手段的多样化与高效化,技术本身脱离人的驾驭或控制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同时在行使权力和维护权利之间设定了一道障碍。国家以保障秩序为务,社会以捍卫权利为要;前者的作用对象是后者,后者需要限制的是前者。二者博弈的结果,常常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启蒙运动以降形成的“人的政治”之终结,则是因为人之所处的悖谬状态:一方面,人需要在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目的与手段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道德与政治之间等方面,既保有基本的平衡态势,又适时地尝试突破。于是,人类在思想与行动上对诸构成要素周全处置的平衡摆,成为人类不至于陷入不可克服的困境的必须。但问题在于这个平衡摆的摆动,无论是频率还是程度,并不单纯受人的意愿控制。因此,当社会控制的天平由技术因素的重大介入而严重偏向掌权者方面的时候,社会的失衡似乎就变得不可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丛的眼花缭乱的进步中,权利的分散利用与权力的集中使用,已经是一个很不均衡的机制,因此,它对现代经典的“人的政治”的终结,便具有结构上的必然性。这不能被归咎于掌权者的心理偏好,而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自然倾向上去理解。
人工智能是技术利维坦吗
启蒙运动以来“人的政治”趋于终结,是两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一股力量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自身演进所形成的;另一股力量便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的政治”的颠覆抑或摧毁。前一股力量乃是人挣脱神的规范或约束之后逐渐形成的,最终在人自身的现代性假设遭遇后现代性的挑战时,以自身的逻辑宣告了这一逻辑的难以为继。后一股力量来自人们对技术的崇尚与迷信,让人们最初以一架精巧的机器所设想出来的利维坦真正变成了一架像人那样精巧运作的机器,结果让“人的政治”的生物-社会人之纯粹性无法维持下去。
从“政治利维坦”到“技术利维坦”
- 小米科技|小米6.66亿元成立智能技术公司 雷军任执行董事
- 量子通讯技术|世界十大重要技术,中国占据四项,排名仅次于美国,震撼了全世界
- 演示|彻底告别实体SIM卡?高通发布"iSIM"技术演示
- 区块链技术|让中国文化用新形式走向世界
- 5g|「技术评论」5G基站回传新挑战,微波能否堪当大任?
- 小米|注资6.66亿!小米成立智能技术公司:雷军亲任执行董事
- 小米成立智能技术公司 雷军任执行董事
- 标杆|中国移动新技术加持天津港5G智慧港口
- 土豆网|阿里文娱转让优酷信息技术100%股份,土豆网接盘
-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统信 UOS 发布国内第一本自研操作系统教材《信息技术基础》